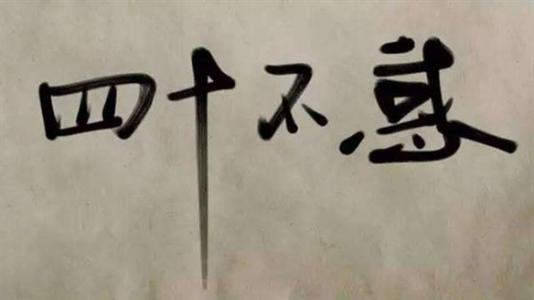故乡的小学
我出生的村子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乡村,叫杜家愣村,小村庄位于渭河的北岸,属于渭河上游,得益于母亲河冲积形成的大块肥沃平原,小村庄哺育了数以千计的村民。
信马由缰一路前行,穿过一户户熟悉而又陌生的院落,不知不觉就走到村小学位置,可惜经过“撤校合并”,这个昔日有朗朗读书声的地方现已经盖起来小洋楼,校口几人合抱不住的大槐树也被砍掉了。
村小学大概在六十年代就设校了,质朴的木牌校门挂在高高的大铁门上,简单而又神圣。小学建筑是典型的中苏合璧式的建筑,完全是靠最早一批老师和村民一砖一瓦修建起来的,建校的艰难可想而知,教室采用大坡屋顶为方便泄水,大坡屋顶上部铺青灰色的长条瓦,这是苏式建筑的特征,下部则是用西北农村特有的檩椽结构支持起来,外墙用的是西北特有的泥巴墙,说是泥巴也完全不对,因为墙的结构是由基子(泥巴和上麦草、草木灰,用特制模具挤压成型晒干,类似于现在的小红砖)砌筑而成的,再在外面粉刷一层厚厚的泥巴,三七墙起步,也可以做得更厚,又笨又重确实不美观但是能保证冬暖夏凉;我们读书的时候玻璃还是稀罕物,万一不小心被打碎了,赔玻璃是基本操作,轻则罚站重则请家长;教室的门窗外框都漆成鲜艳的朱红色,厚重之下不乏活泼,后来工作了才知道这种房子叫做木土混合结构。现在混合结构已经不提倡修建了,就算农村这种房子也越来越少了,村里类似的房子“年轻的”也有三四十年、“年长的”有五六十年却还伫立在那里,但是让人惊叹的是这些“高龄房子”,除了个别屋顶有斑斑漏水痕迹外,甚至还能住人,当年房子的质量之可靠,工匠精神之伟大,可见一斑,比起现在钢筋混凝土房子二三十年就出现的裂缝、不均匀沉降,简直是云泥之别。
一到五年级的教室依次在院子里排开,中间教室外墙上挂着一块砖头大小的薄钢板,旁边墙缝子里面还夹着一根铁棍,对,这就是上下课的敲铃声,手动的,每次都得专人负责敲响,让快迟到同学们胆寒又让期待下课同学们喜欢的铃声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悠扬的铃声伴随着朗朗的读书声,还有远处寥寥的炊烟,组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风景。
学校院子中间是活动场地,对面是教师的办公室,建的稍微好点,红砖平顶,屋顶还伸出来一块挑板,被罚站的时候还能遮光挡雨,后来知道这种房子叫做砖混结构,板用的是预制结构,遮光挡雨的那叫雨蓬。就在如此匮乏的物质条件下,当时学校里面不乏县上教书名师,严厉而又渊博的校长黎校长,和蔼可亲的班主任周老师,胖胖的脸上戴个黑框眼睛的李老师。
而父亲曾经也是小学的民办教师,从以前的老照片和父亲的只言片字中,我了解了些许村小学的曾经的故事:记忆要从七十年代末说起,爷爷奶奶孩子众多,存活下来的有八个孩子,父亲排行老三,前面大姑、大伯、二伯已经分家,众多的孩子让吃饭生活成了大问题,而爷爷的早逝无疑让家中雪上加霜,二十岁不到的父亲带着无限的遗憾上完了初中,高中是不可能上了,养家糊口才是第一位的,入职到村小学成了一名的民办教师。周内父亲给村里的孩子教书上课,周末还要渭河边开垦荒地,种点粮食以补贴家用。因为杜姓在村子里是大户,同宗同族亲戚孩子众多,还有当时读书年龄都普遍大,课堂上喊父亲“三舅的”“三叔的”“三哥的”比比皆是,村子里曾经广为流传的故事就是,那个年代娃娃们普遍吃不饱,也不知道学习,一年级的外甥就是个刺头,又瘦又小还不知道好好学习,一天就知道喊“舅舅”,终于在一次的上课中,舅舅忍无可忍,把这个不写作业不听课的外甥提起来从窗户里面扔到外面的草堆子上,这成了人们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后来这个外甥听话了不少,也顺利的念完了小学。当时随着后面几个叔叔姑姑的长大,再加上自己也要成家立业,父亲在学校这点微薄的收入显然是无法再支撑一大家子的开支了,不得已父亲离开了自己工作十多年的学校,用当时时髦的话说就是“下海经商”了。后面随着政策的落实,坚持下来的民办教师基本都转成公办,最不济也都涨了工资,退休后有了养老金,而父亲再也没能回到学校。前几年父亲病重时,他老人家还念念不忘民办教师的身份和工龄,我曾到教育局咨询过这个事情,可惜撤校这么多年,好多档案没办法找到,这也成了他老人家一辈子的遗憾。
这就是我的故乡的小学,还有曾经在此任教的父亲的故事,斯人远逝,物是人非,唯有怀念聊以安慰自己。
杜志强(笔名辞强),甘肃武山人,现就职于兰州某设计院
故乡的小学相关文章:
★ 故乡,
★ 故乡的小学
★ 故乡的“山河”
★ 被我弄丢的你
★ 悲凉的黄昏岁月
★ 东北行之一